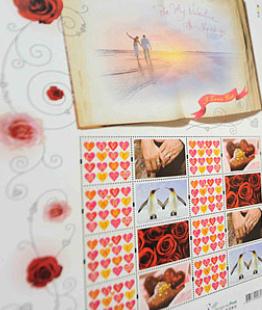和尼玛拉木一起上邮路
大家好!我叫叶娜,是《中国邮政报》云南记者站的记者。在采访工作中,有这样一首小诗和诗里的主人公,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我
把思念送给你
把祝福送给你
把希望送给你
把世界送给你
我
把崎岖留给自己
把艰辛留给自己
把危险留给自己
把孤独留给自己
历史
正渐渐把我忘记
而雪山峡谷
却永远刻下我默默的足迹
这是一位网友在人民网上,为一位藏族乡邮员的事迹所感动而写下的一首诗,诗里的主人公就是尼玛拉木。
2004年和2008年,我先后两次赴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尼玛拉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采访她,并同她一起上路送邮件。曾经走近拉木的我,对这首诗里的感动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对这短短十几行文字背后,尼玛拉木十年如一日行走在雪山峡谷乡邮路上的这份坚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别样的感动。
每当我念起这首诗,眼前就会浮现出尼玛拉木身背邮包从大山中艰难迈步而出的疲惫步伐,浮现出她逐渐消失在悬崖峭壁间的孤单背影,浮现出那无助地悬挂在细细溜索之上的瘦小身躯……思绪把我又拉回到了第一次和拉木上邮路的清晨。
2004年10月底,正是迪庆高原秋寒料峭的时候,我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澜沧江边的云岭乡采访尼玛拉木。
天刚蒙蒙亮,站在尼玛拉木每次出发的山路前,望一眼足有60度的荒坡,我声音颤抖,嘀咕着:路呢?路在哪里?拉木随手指着山上被羊蹬出的一片乱石坡说:“这不就是吗?”可这是什么路啊?坡面上都是凸起的石块和碎石,看起来到处都是路,却又无从下脚。犹豫之间,拉木已背着两个硕大的邮包爬到了我们“头顶”上,山势太陡,我的头几乎要碰到她的脚。没有可抓的地方,鞋底一直打滑,蹭下的碎石“哗哗”往下掉,我只好趴下身来降低重心,手脚并用艰难地往上爬。央视的记者打趣道:“没想到,来云岭咱们都变成了猴子。”
好不容易爬上了荒坡,刚刚用脚踏实走了几步,转过一个山脚,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窄窄的山路,一侧是峭壁,一侧是万丈悬崖。山风呼啸,人都站不稳,我不敢低头往下看,偶尔被脚下的石头一绊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在这样的悬崖边行走,随便打个踉跄都是极其危险的,只要一脚踏空,摔下去就粉身碎骨。
突然,走在前面的拉木回头冲我们喊:“小心,上面有山羊,羊蹬下的石头会打死人的!”话音刚落,几颗小石子就在我们前方不远处飞落山谷。大伙的心里更紧张了,不由自主地往里靠,感觉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些。
更要命的是,一路上,本来就很窄的羊肠小道时常会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踪影,面前只剩下山岩塌方后一泻而过的痕迹,人踩出的小路被塌方的石块拦腰截断,我们都打住了脚步。只有拉木接过记者手中的摄像设备,小心而娴熟地先走过去,又转回来接我们。尽管脚下的悬崖令人胆战,我们还是在拉木的带领下,硬着头皮,半蹲身子,扒着山岩,半步半步往前挪。待到了对面小路上,我的手心都沁出了冷汗。接下来碰到的塌方更糟,石块坠落后留下的全是松软的淤泥,可这也没难倒拉木,只见她从旁边搬了些石头扔到淤泥里,踩着并不稳当的石块飞身而过。可我们实在不敢在悬崖峭壁间做这样冒险的动作,只好绕道跟上拉木。
是啊,如此险峻的山路,我们偶尔来一次就害怕得要命,而拉木呢?她瘦小的身躯还要背着40多斤重的邮包频繁地往返其间。要是碰上雨天或下雪,我真不敢想象在如此险峻的山路上该如何行走!然而,这就是尼玛拉木每次送信的必经之路。我不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孤身一人长年累月奔走在如此艰险的悬崖峭壁间?
我们的采访明显拖慢了拉木的脚步,我向她表示歉意,可拉木笑笑说,今天她很开心,因为有我们做伴路上就不寂寞了。是的,邮路上的拉木是寂寞的,那天我们走了大半天,只碰到了一个赶马人。一个人的邮路危险又寂寞,但与拉木在村里、小学校受到的欢迎相比,这些算得了什么呢?才到村口,就有老乡不停地和拉木打招呼;穿着民族服装的老阿妈,沏好酥油茶拉她进屋歇脚;藏家大姐放下手里的活儿,捧出新收的藏梨请她品尝;刚进学校,孩子们就高兴地围上来,有的翻翻拉木的邮包有没有新鲜的东西,有的围着她问这问那。这时的拉木就一改羞涩的本性,笑得轻松自然、惬意满足。穿行于藏家村寨,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拉木和老百姓的亲,我忽然明白,那份支撑尼玛拉木的力量就在老乡们期盼的目光中,就在孩子们开怀的笑容里!
一位名叫永金的老阿妈每次见到拉木都特别高兴,因为她的几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从儿子们开始上学直到工作,都靠拉木带来的信件联系着。因为老阿妈不识字,拉木每次把信送到后,都要帮她念信。每当念完了新的信,老阿妈就又把以前的信翻出来让拉木念。看得出来,她对儿子的牵挂就在这一页页发黄的信纸间。看着火炉边永金阿妈面对拉木那如同自己儿女般慈祥的笑脸,我意识到,拉木不仅仅是一名邮递员,而是一个情感的象征,是藏民们维系亲情的纽带,是乡亲们沟通山里山外的桥梁!
回到拉木家,我悄悄问她老公阿史布:“邮路那么危险,拉木一个人在外面跑,你们放心吗?”阿史布说,怎么可能放心啊?拉木当上投递员不久,就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伤过,被蛇吓过,过溜索时她也很害怕,家里人总担心她路上出意外。后来,拉木上邮路就经常穿着红色的衣服,因为在山里红色是最显眼的。有时候,拉木路上受了伤,往伤口上洒把灰土止住血又继续送信,可是回到家里帮她清洗伤口时,用夹子一点一点把伤口里的泥沙掏出来,拉木常常疼得忍不住叫出声来,阿史布说:“那声音一阵一阵揪着我的心,让人不忍下手!”
哦,那一刻我才体会到,原来拉木也并非一开始就能安心地走这条邮路,她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担心过,害怕过,甚至受伤过。只不过为了工作,她必须让自己变得坚强,必须让自己习惯艰苦、适应孤独,必须让自己勇敢地克服困难、面对危险,哪怕是滚滚澜沧江上命悬一线的细细溜索也要飞身而过!那一刻,我明白了,是邮路磨炼了拉木,也是邮路铸就了拉木坚强的性格!
2008年3月,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媒体对尼玛拉木的事迹进行采访、调研,我再次来到了云岭乡。时隔4年,拉木还好吗?她的工作和生活有变化吗?
再次和拉木一起上邮路,我发现澜沧江上修起了吊桥,拉木送信不用再过危险的溜索了;更多的村子通了公路,拉木有时可以搭车送信了;拉木的邮件也更多了、更重了,有时连邮包都装不下了。可是不变的是拉木工作时认真负责的态度,是老乡们对拉木的热情,是学校里孩子们开心的笑容,是儿子看着妈妈背上邮包出门时的依依不舍。
有一天,我在拉木家看她的照片,忽然听到拉木问我:“叶记者,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白,看看我,连照出相片来都是黑黑的。”我没想到拉木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回过头端详着眼前的拉木,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忽然觉得很心疼——可不是吗,这是一张只比我大两岁的女人的脸,可是岁月却过早地在上面刻下了风霜;这是一位爱美的藏族姑娘,可是她却甘愿长年累月奔走在气候恶劣的雪山峡谷间任凭风吹日晒;这也是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可是在荣誉的光环背后,这颗装满母爱的心里却有着许多的不得已和酸楚。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同事王寅戟给我讲过的一件事。2006年,拉木来昆明作事迹报告,报告会后,她要我的同事王寅戟带着她到肯德基买个鸡腿。王寅戟让她尝一块她却不舍得吃,小心翼翼地将鸡腿包好,说要带回去给儿子。她说:“我经常在外面跑,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少。有时送信回家太累了,想听儿子叫声妈,可儿子倚在门边,就像看到一个陌生人,我想带个肯德基的鸡腿回家,让儿子高高兴兴地叫我声妈妈。”
在采访拉木的路上,我隐隐感到有时拉木好像有心事,似乎我们的随行并没有带给拉木4年前那样的快乐。省电台一位记者采访尼玛拉木时,她突然哭了起来。她说:“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上级却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比我更辛苦、更艰难的邮递员很多,你们应该去采访他们。你们老采访我,我的工作干不完了,老乡们都还等着我呢。”原来,她是为了这样的原因而不开心!如果换做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机会,高兴都来不及,哪里会有拒绝的说法,而拒绝的理由却是怕影响工作这么简单。原来,拉木的荣誉感并非来自那一本本大红的荣誉证书,而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不能让乡亲们失望!
和尼玛拉木一起上邮路,我看到一个并不强壮的女子,在10年的岁月里,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认真做一件事,那么执著,那么坚持。我也看到一个人,曾经是那么的出名,她的事迹发表在众多的报刊上,接受了很多表彰,但是热闹过后,她仍然坚持走在自己熟悉的山路上,默默无言。
——藏民们行走在这条艰险的路上,那是信仰的驱使,也许他们数年才经历一次;
——探险者行走在这条路上,那是发现的渴望所驱使,对于他们或许一生就那么一次;
——而尼玛拉木则是邮政事业和责任的驱使,一天天、一年年行走在这条路上。
她的身影陪伴着群山,她的青春在峡谷中流淌!她让我深深地感动!
如今,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眼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和尼玛拉木一起上邮路的一幕幕——她身背邮包艰难地穿行在雪山峡谷间的瘦小身影,她在滚滚澜沧江上飞渡溜索的惊险瞬间,都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激励着我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克难奋进,乐观向上!
更多关于 尼玛拉木 的邮政新闻
更多关于 尼玛拉木 的站内信息
本站部分文章转载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您的权益,请Email和我联系!